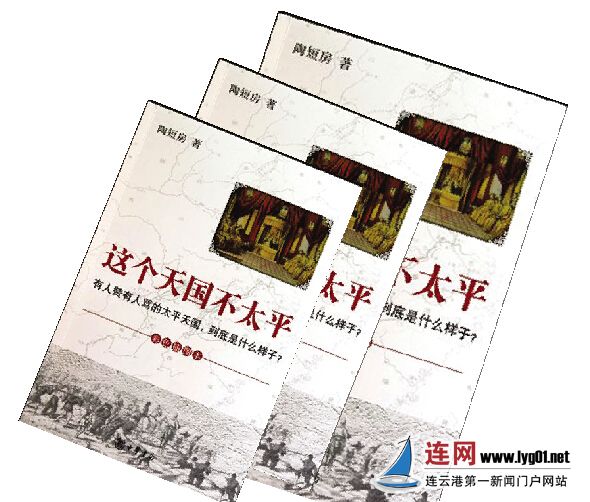
【连网】(记者 刘安琪) 历史学在中国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想要研究真正的历史,另一方面又要满足执政者的政治需求。两相比较下来,服务于政治就常常成为第一标准,尊重史实则成为第二标准。这导致许多历史研究过于随意化,在评价与史实还原方面都有意无意地进行不定程度的重新编造。
尴尬的历史学
历史学在中国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想要研究真正的历史,另一方面又要满足执政者的政治需求。两相比较下来,服务于政治就常常成为第一标准,尊重史实则成为第二标准。这导致许多历史研究过于随意化,在评价与史实还原方面都有意无意地进行不定程度的重新编造。
太平天国的研究也是如此。由于它是近代史上中国最大的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农民战争,它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需求。普通读者看到的太平天国是激情的、上进的、被残酷扼杀的、反压迫的农民军队,这支军队几乎有着先进的指导思想与政治诉求,等等。很多人更是被灌输进太平天国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等观念,使太平天国几乎成为一个臆想出来的天上人间。
然而,真正的太平天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陶短房先生的《这个天国不太平》试图匡正人们对太平天国的误读,使一个尽可能真实的太平天国展现在人们面前。然而陶先生是不承认有这样的雄心的,他只是希望“作为后来人,我们既不是清廷,也不是太平天国的史官,无需、也不应穿越到那个时代,以其中一方的是非为是非,更不应‘替古人操心’,绞尽脑汁地将自己的是非强加给读者。之所以起意写这一组和太平天国人物有关的文章,便是想试着跳出总围绕着‘好人’、‘坏人’转圈的史评怪相。”陶先生也希望人们从多角度去考量历史。“历史是复杂的、多元的、多色彩的;每个人的言行、取舍,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效果,一种评价。”
家庭八卦与太平虚幻
书中很多观点与教科书的观点不一致。比如:太平天国其实并不是男女平等的,并不是女兵与男兵一起上阵打仗的,洪仁玕并不是那么资本主义的,洪秀全一开始并没有想要起义的,等等。
本书并没有从正面去讲洪秀全,却几乎从各个侧面都讲了洪秀全。他在书中几乎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在。关于洪秀全的文章与解读实在太多了,正面的、负面的都有,但从与洪秀全有关的那些人和事,以及太平天国的方方面面所呈现出来的洪秀全精神就不太多,或者普通人不太容易看到。
于是,陶先生先从洪秀全的女人们开始来讲这样一个不太平的天国。书中讲洪的正妻赖莲英为什么不叫王后,为什么排名老二,为什么叫“又正月宫”等等,甚至探讨了洪秀全到底有多少个老婆这样一个八卦的问题。
在研究了女人的多少后,陶先生提出女人对洪秀全来说并不重要,是“低值易耗品”。虽然陶先生没有再继续往下说开去,但仅从洪对女人们的粗暴及随意处置上,那个“男女平等”的幻想就被现实击碎了。
陶先生此后讲了洪秀全的子侄、驸马,以及人们在影视中经常看到的洪宣娇。他对洪秀全育子不屑一顾,并在研究后说,“今天保留下来的洪天贵福(洪秀全的儿子)供词、诗句、错别字连篇,文理不通,本身是小知识分子的洪秀全,居然将自己的继承人教成十五六岁都无法写出通顺文字的文化低能儿,着实令人惊诧”,“清军许多官兵对这个连骡马都分不清、籍贯也说不明白的‘弱智少年’(洪天贵福)身份十分怀疑。的确,‘首逆’智商如此低下,实在令他们匪夷所思”,接着他又引王庆成先生的诊断道,“洪秀全是否‘虎父’,见仁见智;但洪天贵福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犬子’”。
洪秀全对他的子侄很是重用,有的在襁褓中就被任命为要职,一批批的“侄子大军”都不满10岁。
打不来太平的武将文官
对于石达开、冯云山、韦昌辉、萧朝贵、洪仁玕等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陶先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尽量用史实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他对石达开是抱以同情的,并说“如今100多年过去,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时而上天,时而入地,可谓褒贬不一,但绝大多数人对石达开仍寄托深切的同情。”这些同情里有陶先生的一份。在对石达开的论述中,陶先生特意强调了一下石达开“干女儿”的问题,并认为“干女儿”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是好事者编造的谎言罢了。
对于民间评价较高的冯云山,陶先生则认为冯云山并没有想像中那么憨厚老实,而是“有叛逆思想”的滑头,煞费苦心地“把根本没在身边、甚至当时还不想造反的洪秀全扶为一把手”,为的是“容易聚集人马”,使人们有敬畏感。
在谈到冯云山之死时,陶先生说,“当地的口碑称,太平军本不打算攻打全州,准备绕城赶路,城上一名清朝低级军官一时冲动,对城下太平军一顶黄色轿子开了一炮,结果太平军一片哗然,不顾伤亡猛攻全州16天,终于攻破———轿上坐的正是当时已封为南王的冯云山。”这段记载颇有传奇色彩,虽不知具体情形之真假,也很难考证,但就其绘声绘色的程度而言,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书中还有段比较有趣的记载,说冯云山曾坐牢,“在坐牢期间,冯搞出了一个‘太平天国天历’,这本闭门造车的历法既没有闰年,也没有闰月,大月31天,小月30天,40年‘一加’,加年每月都33天。这样的历法‘均匀圆满’,看上去很完美,符合洪秀全的口味,却很不符合科学———该立法推行六七年后,太平天国的‘中秋节’月亮却仍是个月牙儿,莫名其妙以至于恼羞成怒的太平军将士据说有的迁怒于月亮,竟用弓箭射、火枪轰,以泄‘不圆’之忿。”这段记载很有意思,可见太平天国在起事后,虽然轰轰烈烈,但在历法等制度建设上却相当儿戏,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不得不感慨其失败从各个层面上看都是必然的。
关于萧朝贵,则是相当有戏剧色彩。他的出场很滑稽,也很政治。他通过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方式确立自己的地位,怪不得陶先生说“与其说为了‘革命需要’,毋宁说是为了他自己的需要:作为拜上帝会通神人物的后起之秀,他必须用这样的非常手段,才能后来居上,占据梦寐以求的高位。”后来,萧朝贵地位一年不如一年,“是由于他的才能与胸襟达不到该有的高度,是与其能力相称的”。关于萧朝贵的故事,陶先生用了个讽刺的笔法写了一段,这里也忍不住摘出来:“他最后一次、也是导致‘英勇负伤’的一次,是在永安州城中,当时城池被清军围困,后勤发生困难,士气不高,他‘奋勇上阵’意在鼓励,却不料从椅子上摔下,跌伤了颈椎,休了几个月病假。”
许多历史专家及民间舆论历来对洪仁玕的评价比较高,但陶先生显然不这么看。他一方面肯定了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一方面又说他“是个具有强烈两面性的政治角色”,“先进性和落后性戏剧性地集于一身”。洪仁玕“能提出各种精辟的见解,却缺乏坚持和推动的勇气”,见风使舵的本领也超强。他始终与洪秀全的意志保持高度的一致,往往提出了一个目标,在行为上却往相反的方向前进,比如,“他主张严格控制官员提升”,可他一次性就保举了几十人升官,并在9年里,使五爵多达2700多个,“至于六爵、丞相,已经多到数都数不清的地步”。这样的一个人物,在历史上仅凭一个《资政新篇》就被高度赞扬,显然有失公允。虽然评价各有不同,但至少应该在亮出其先进性一面的同时,将其落后的一面也同样呈现给读者。显然,这是本书做到的,也是与传统教科书式的文章有所不同的。
其实,文官在太平天国是不受重视的,文官系统里有文化的人并不多,“秀才以上学历的似乎只有一位:夏官正丞相何震川”。他的主要工作是每月写一本洪秀全语录,以及“删改四书五经,比如把‘唐太宗’改为‘唐太侯’……将经史里的‘酒’都改为‘茶’(洪秀全禁酒),等等。”文官在太平天国的地位之低下,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干王府最重要的文官———六部尚书,其办公地点就在一个煤炭仓库的楼上”。
读书人在太平天国是不受器重的,前面提到了一点。陶先生又展开讲了许多,比如太平天国一年四次科举,录取率极高,不到1000人的考生里,中举的多达800人,但读书人仍旧不愿意参加“高考”,以“故意写错字、涂改,‘自动被淘汰’”的手段来逃避,“以至于很多地方,太平天国的地方官不得不强抓考生,武力押送赴考”。